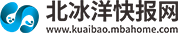研讨|昆明作家群:边地,或中心:天天关注
最近,由中国作家网、昆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从西南崛起——昆明作家群北京研讨会”与“边地,或中心——昆明作家群与北京作家群对话活动”举办。北京的学者与来自昆明的六位作家——张庆国、陈鹏、半夏、包倬、祝立根、胡兴尚进行对话。研讨会中,每位评论家有针对性地点评两位昆明作家的创作,作家们也予以回应并畅谈了自己的创作感受。
在描述对于云南文学的总体印象时,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以“远方的上方有一片灿烂的文学风景”来形容。在他眼中,云南拥有烂漫壮观的高原自然景观,也因为深深扎根于云南大地之上生发出来的独特的文学景观。他表示,云南的出版人、作家对所处这片土地的自我认识和建构使得他们的作品都极具辨识度。作为研讨对象的这6位昆明作家也正是这一从西南崛起的云南作家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这6位作家中,张庆国的创作体量丰厚而庞大;半夏的写作在当代散文和非虚构创作中呈现出独特面貌,她关注山川风物、鱼虫草鸟等一切大地上的生命;陈鹏的作品具有实验性和形式感,有种具有创造性的锐利感;包倬的创作体现出一种幽默感和对现实敏锐的捕捉能力。这次与会研讨的还有两位诗人胡兴尚和祝立根,因此从文体上来讲,6位昆明作家中有小说家、非虚构作家、诗人,构成了一种互相映照的镜像般的关系。
活动现场
“不安分”的云南,刺痛庸常
张庆国的创作始于1980年代,“年轻时候总是雄心勃勃,希望写出伟大的作品。”张庆国说,那个时候,他热衷于先锋式的写作,不过近几年,他的文学观点发生了转变,作品选择更多地“落在实处”,他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犀鸟启示录》今年获得了第九届徐迟报告文学奖。这次,张庆国提供了《马厩之夜》《如鬼》《黑暗的火车》3个小说文本。其中,《马厩之夜》是一部指向历史深处和生命本身的文本,在叙述的方式上具有很强的探索性。
学者顾建平认为,张庆国的小说中有突出的对于城市中非主流、半边缘人物的书写;评论家张莉认为,张庆国的故事里有明亮的一面和黑暗的一面,同时进行明暗缠绕的叙述,正如《马厩之夜》中,家族故事里影影绰绰地体现出内在的复杂历史性。
云南是一片多民族聚居的土地,它的地方性与民族性是不可分离的。彝族作家包倬的作品中就有强烈的地方性,但是这种地方性不是风光化的书写,而是民族性的书写。张莉认为,包倬致力于探寻少数民族精神意义上的意志性的东西,不回避他的地方性、民族身份。在《双蛇记》中,父亲挣扎在精神痛苦中,当他回到家乡“阿泥卡”村才得到了治愈。“阿泥卡”出现在包倬的许多作品中,“可以说,阿泥卡是包倬的文学之乡。”张莉说。
许多青年作家的写作可能面临一些困境,如迷失在炫目、玄妙的叙事和语言、技巧以及混乱情绪的表达之中,但作品却缺乏一个内核。李蔚超认为包倬克服了以上的问题,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叙事风格,找到了独特气质的小说表达,语言有力量,短促而准确。
与包倬相比,陈鹏离开了“阿泥卡”,离开了西南,他的写作引入了一种世界气象。丛治辰读《麋鹿》时,没有想到故事竟然发生在巴黎。丛治辰对陈鹏最初的印象是他对于先锋、实验的热情和笃信。小说《麋鹿》一直到结尾都没有解释麋鹿象征着什么,可是在小说的描述当中,这头麋鹿是这么迷人,它以一种极其突兀的形象插入到小说平平无奇的日常场景中,这个形象并没有发挥叙述性的作用,可是却作为一个意象“横插”在那里,让我们疑心加缪之死和麋鹿有什么关系。
关于先锋性与实验性,顾建平与陈鹏一直持不同观点。在顾建平看来,小说在当下的疆土已经十分广博——它借助电影、心理学的意识流,借助新闻、纪实文学的形式,它从魔幻、荒诞等现代主义思潮中学到了“无聊”,从后现代主义悟到了平面化、无声、无意义……小说的形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也许现在的重点是在现有的领域中不断深耕,探索‘新的形式’并不是一种必要。”顾建平说。陈鹏则认为影视作品对于重复的故事性的叙述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占领性优势,而小说家应当对故事写作保持足够的警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小说的叙事要抛弃故事性,相反,他认为小说家可以不讲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叙事要有故事性,要有“勾引”读者读下去的动机。
靠近太阳的土地:诗意的、自然的
半夏是从一只绿头苍蝇开始对虫子的观察和拍摄的,用手机拍下来后,她惊异于这样一只小生命的美丽。此后她走进旷野、荒原,观照虫子、观照自然、观照万物。这样的观察持续了五年半的时间,形成了《与虫在野》这本书。
“这不是一本关于虫子的科普读物,这样的写作是一种博物学意义的。对它有兴趣,去感悟它,把它描述出来,这就是博物志最初的写作。”半夏说。徐可在多年前就读到过半夏的散文集《与虫在野》,认为她的作品着眼于山野之间的小虫、小花和它们所带来的真挚和美好,秉着对动物、植物的关爱之情深入阐述了生物周期的节律,让我们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温情。《与虫在野》对女性写作也有着重要意义,张莉表示,女性写作主题常常围绕着爱情、婚姻、家庭,而半夏在田野中寻找到自己的一方天地,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书写的领域。
胡兴尚是此次研讨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位,他出生在云南乡间,做文学期刊编辑之前在泰国当过汉语教师,在国内中学做过高中语文老师,在基层政府工作过,也驻过村。诗歌陪伴他辗转于乡野、异域、远郊、都市,而不同时期的诗中,也有水土的不适、人际的惶惑、生活的惘然、莫名的不安。他表示,无论是经验写作还是直觉或形而上的写作,诗歌的生成都借着某种当下和在场的力量,与特定时空相呼相应。
活动现场
当谈论“边地,或中心”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在“边地,或中心——昆明作家群与北京作家群对话活动”中,作家们也就文学的地域色彩、中心意识或去中心化、当下异质性写作的困境和可能、作家如何走出“影响的焦虑”等议题展开研讨。
文学中的边地或者中心可能是个伪命题,对作家而言,最重要不是在边地或者中心,而是写出真正有分量有力度有影响力的作品。作家赵兰振认为,即便身处边地,作家也能写出伟大的作品,比如《圣殿》《我弥留之际》《喧哗与骚动》《村子》等都是在一个“邮票大小”的小镇完成的。所以,作家的文学创作与边地或中心并无太大关系,只与作家的才华和对文学的认知与定位有关,作家应该提高对文学的认知和品位,用心灵审视现实生活,通过故事呈现出来,建构属于自己独特的文学世界。如果存在边地,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边地写作,可能具有了展示独特地域和独特生活的更大优势和更多可能。
云南诗人胡兴尚认为,从更长的时间来看,伟大文学作品诞生的地方应该就是文学的中心,比如福克纳的奥克斯福小镇,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麦克劳德的布雷顿角等,都可看作文学的中心。所以,当我们在谈地方性写作的时候,我们如何看待所生活的土地、如何避免惯性的或者无效的写作、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展现地方的独特性,这是摆在所有写作者面前的难题。
80后陆源是壮族作家,他从语言角度谈到,边地或中心的外延其实非常丰富,在他的家乡,着火不写成“着火”,而写成“走水”,这种语言的独特性势必会影响作家的写作。当然,作品呈现异质性的同时也要兼顾普遍性,纯粹的异质性写作会流于符号化,无法完成文学交流和对话。
在李朝德看来,边地或者中心的概念,其实都是相对的。相对于北京,昆明处于“边地”,相对于整个云南,昆明又是中心,出发点不一样,结论就不一样。不管如何,我们热爱文学,对文学的内在要求都是一样的,即便我们的文学外在表达和形式不一样,但它内在的美学标准和美学追求是一样的,是统一的。而地域文化的千差万别,又会给文学带来更为丰富多彩的面貌。
-
研讨|昆明作家群:边地,或中心:天天关注
研讨|昆明作家群:边地,或中心
2023-04-11 -
煤炭板块跌幅居前,PVC成本支撑走弱
壹 PVC期货震荡下行,煤炭板块大幅下跌煤化工市场整体表现欠佳,...
2023-04-11 -
世界聚焦:最衰卫冕冠军锋无力,补强锋线,AC米兰相中西班牙国脚前锋
AC米兰比领头羊那不勒斯少了22分,放眼整个五大联赛,卫冕冠军联赛...
2023-04-11 -
最新资讯:被湖南暂停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合作 渤海银行株洲分行最新回应:已采取有效措施,妥善解决问题
【被湖南暂停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合作渤海银行株洲分行最新回应:已...
2023-04-11 -
全球今热点:凌霄泵业: 年度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审计报告
凌霄泵业:年度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审计报告
2023-04-10 -
核酸咽拭子是什么 核酸咽拭子是什么材料做的
1、核酸咽拭子检测是一种医学检测方法。2、是用医用的棉签,从人体...
2023-04-10 -
RUDY伙伴美利达挑战者,周末2天拿下多个自行车赛冠军!|世界看点
4月8日、9日两天,多地举办了自行车赛事。我们的伙伴美利达挑战者拿...
2023-04-10 -
怀旧经典游戏第十二期:火影忍者手游罗砂高端教学,助你提高打法意识-今日看点
火影忍者手游通过真实还原了漫画中角色的动作、特技和技能,让玩家...
2023-04-10 -
纽扣电池行业发展规模分析及纽扣你电池行业前景分析
目前高端市场耳机电池单价为15-18元RMB,中端市场为15元,低端市场...
2023-04-10 -
景区骆驼被轮番棒打屈膝求饶,目击者:骆驼嘴被打肿流血,很心疼
4月9日,河南商丘。李女士爆料,在一景区看到工作人员轮番棒打骆驼...
2023-04-10 -
钱的真相?:天天速看料
钱的真相?,快乐,爱情,喜悦,潜意识,稻盛和夫,性格决定命运
2023-04-10 -
【新要闻】英雄联盟设计师:年中将发布全新2v2v2v2游戏模式!
今日英雄联盟设计师团队官博更新,发布英雄联盟执行制作人Brightmoo...
2023-04-10 -
环球热讯:奔驰最高降价20万!湖北车市价格战持续,传统汽车大省发生了什么?
东风日产、东风雪铁龙、一汽大众、广汽本田等传统车企各占山头,奥...
2023-04-10 -
天津医科大学图书馆查新_天津医科大学图书馆
1、图书馆环境还可以,除非考试节假日,都开放的,馆内有空调,开闭...
2023-04-10 -
世界快报:百色走进深圳推介大健康文旅产业
4月6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2023年“深情百谊融湾区潮玩壮族三月...
2023-04-10 -
强=͟͟͞͞沙=͟͟͞͞尘=͟͟͞͞暴=͟͟͞͞来=͟͟͞͞袭 陕西刚刚发布大风蓝色预警
强=͟͟͞͞沙=͟͟͞͞尘=͟͟͞͞暴=͟͟͞͞来=͟͟͞͞袭...
2023-04-10 -
每日热门:「稳增长 促发展 强信心——拥抱民营经济发展的春天」三一:打造世界一流企业
编者按民营经济是湖南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在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湖南...
2023-04-10 -
每日热文:胡塞武装与沙特会谈讨论永久停火,联合国特使:和平的真正机会
当地时间2023年4月9日,也门萨那,阿曼和沙特代表团会见胡塞官员。...
2023-04-10 -
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前景思考|天天热议
在支付基础设施成熟的条件下,我们估计数字人民币的内地-香港双边跨...
2023-04-10 -
上海城市展区第三次亮相消博会,天文钟、大白兔、LED橱窗秀……亮点不断
4月10日至15日,世界目光聚焦海南,第三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将在...
2023-04-10 -
天天讯息:又看“繁花似锦”,第三届湖南女画家作品邀请展开幕
花团锦簇,岁月温柔。4月9日,第三届 "繁花似锦 "——湖南女画家...
2023-04-10 -
肝硬化传染吗怎么传染_肝硬化传染
1、肝硬化传染吗?我觉的这个更应该区别的对待,因为形成的原因是不...
2023-04-09 -
焦点要闻:苹果电脑复制键和粘贴键_复制键和粘贴键
1、CTRL+C复制CTRL+V粘贴CTRL+X剪切。2、在打开的2个文件夹窗口中可...
2023-04-09 -
播报:正源股份: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比例超过1%的公告
正源股份: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比例超过1%的公告
2023-04-09 -
盾安环境:2022年净利润8.39亿元,同比增106.98%
盾安环境:2022年净利润8 39亿元,同比增106 98%:盾安环境业绩快...
2023-04-09 -
孟菲斯动物园为“丫丫”办告别派对 网友:祝一路平安
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8日,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动物园为将返回中国的...
2023-04-09 -
白马西风塞上下一句_白马西风塞上
1、白马西风塞上:塞北的草原。2、杏花烟雨江南:江南水乡。3、雾锁...
2023-04-09 -
世界快讯:昆虫记主要人物和主要内容100字_昆虫记主要人物
1、1823年-1915年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jean-henricasimirfab...
2023-04-09 -
环球头条:他是汉室江山最牛的家族,号称皇后专业户,连唐朝李世民也有关系
他是汉室江山最牛的家族,号称皇后专业户,连唐朝李世民也有关系,对...
2023-04-09 -
前拜仁后卫博阿滕自由加盟法国里昂
前拜仁后卫博阿滕自由加盟法国里昂,合同到2023年。32岁的博阿滕在...
2023-04-09